| 从胡瑗到王艮:两位泰州人引领儒学走向大众明体达用 |
| 发布时间:2023-10-23 10:49 |
信息来源:社科联 |
|
儒家重视教化的传统,使其从诞生之日始就带有面向大众、面向民间的基因。尤其是进入宋代以后,整个社会的平民化倾向,使得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从某种角度说,就是其在与民间大众的互动中,不断摆脱传统经典章句的束缚,重新找回个人主体性和思想独立性,逐步走向世俗化的过程。胡瑗以及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作为泰州历史上的文化名人,透过他们恰可为探析儒家思想从宋初到晚明的这种世俗化嬗变提供一个独特视角。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人称“安定先生”,他与孙复、石介一起并称为“宋初三先生”,被认为是宋明理学的先驱。北宋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和门阀士族的解体,一个主要以庶族地主为中坚的新型士人群体逐渐形成。与贵族化的旧士族相比,该群体平民色彩比较浓厚。作为一个复合型阶层,他们介于官民之间:或进而为官,经由科举步入仕途;或退而为民,成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正因士人群体的这样一种独特地位,使得他们成为沟通官民,促进不同层次文化上下交流的中介力量。 胡瑗就是该群体中的一员,他出身寒微,科举受挫后到山东泰山栖真观苦读十年回到家乡,在泰州城内华佗庙旁的经武祠讲学,又“以经术教授吴中”,受时任苏州知州的范仲淹之邀,在其创建的苏州郡学中任郡学教授。由此,胡瑗从民间私学进入官学系统。后又应湖州知州滕宗谅聘请,主持湖州州学。他开创的“苏湖教法”,“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晚年又在太学任教七年,直至东归病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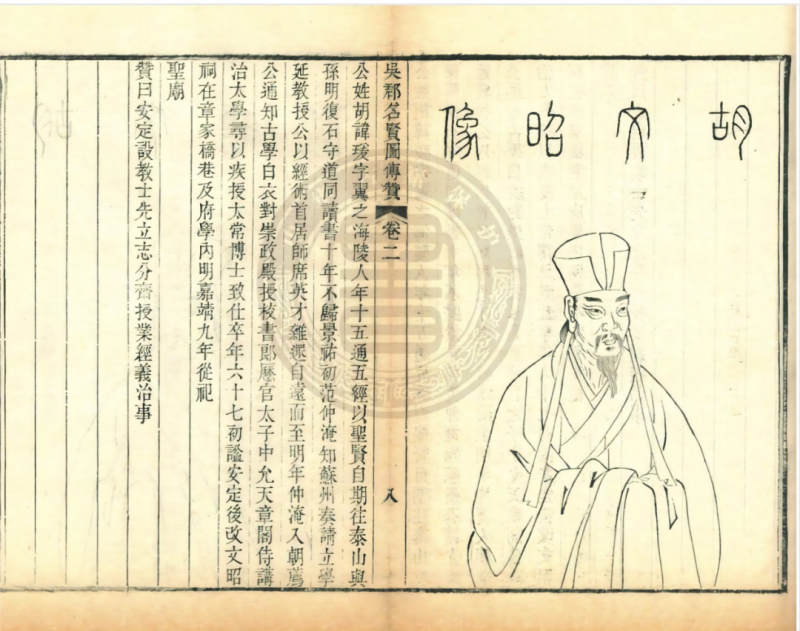
《吴郡名贤图传赞》,(清)顾沅辑,清道光七年(1827)长洲顾氏家刻本,天津图书馆藏 所谓“苏湖教法”,就是胡瑗在苏、湖两州教学期间所创立的,以“明体达用”之学和分斋教学法为代表的一整套思想理念和方法。当时,科举制度已成为广大中下层士人向社会上层流动的主渠道,他们进入官僚系统,固然带来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新气象,但也有不少“苟趋利禄”之辈,专习浮华声律以应试,入仕后成为只知一味享乐的庸官。面对社会结构巨变所带来的“信仰危机”,胡瑗强调教化的重要性,提出了“明体达用”的思想,这里的“体”就是儒家的基本道德精神;所谓“用”就是将所学运用于实践,治理国家。通过在民间私学和官学的讲学,胡瑗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而由此形成的自由讲学传统,被后世学者所发扬,成为宋明理学传播的主要方式。 从孔子开始,讲学一直被儒家认为是传承文明、积极入世的具体体现。但到了汉代,儒家学术逐步陷入章句化和贵族化。日渐繁琐的经学考据,使其只能主要以远离世俗大众的精英文化形态,局限于宫廷和书斋。汉学经义尤重家法与师法,强调疏解经义时“注不驳经、疏不破注”。而作为来自民间的学者,胡瑗的学问并没有受其束缚。他在私学和地方官学,面对广大基层士庶讲学时所养成的治学风格,使其更注重自己对人事物理的内心体悟以及对儒家经典的个性化阐发。他的《周易口义》《春秋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等主要著作均以其口头讲述,由弟子记录课堂笔记的形式流传于世。在讲学过程中,胡瑗不拘泥于前人注疏,凭己意对经典的义理加以发挥,开宋学以义理解经之先河。他这种“以圣贤自期许”,敢于疑经惑古,自创新解的精神和对“明夫圣人体用”的强调,实质上是以孟子的“性善论”为逻辑前提,向世人宣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与古代圣贤相通的,普通人一样具备成为圣贤的潜质。这种与前人相比更加突出个人主体性的治学风格,又恰好适合用讲学这种口头评议的方式表达出来。在整个社会趋向平民化,儒家文化由一种传统的精英文化逐步走向庶民大众和世俗生活的背景下,随着讲学活动的重新兴起,儒家思想就此迎来了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期。 由于儒家学者通过讲学等手段,对教化士庶、化民成俗理想的躬行力践,加上科举的促进,以及印刷技术的成熟,儒家文化在民间迅速普及,客观上又为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平民化和大众化铺平了道路。 元明以来,儒家文化的这种世俗化转型逐步得到官方认可,以程(颐)朱(熹)一系为代表的理学作为国家意志,成为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并随时间的推移走向教条和僵化。王阳明的心学在明代中叶的兴起,为当时的思想界吹进了一股新风。而将“心学”思想推向极致,将宋明理学彻底世俗化、大众化的,就是由王阳明弟子王艮所创立的泰州学派。 王艮(1483—1541),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与胡瑗相比,王艮更是来自社会底层,他灶户出身,靠贩卖私盐起家。师从王阳明后,由于其“有疑便疑,有信便信,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使其“时时不满师说”,甚至“往往驾师说之上,持论益高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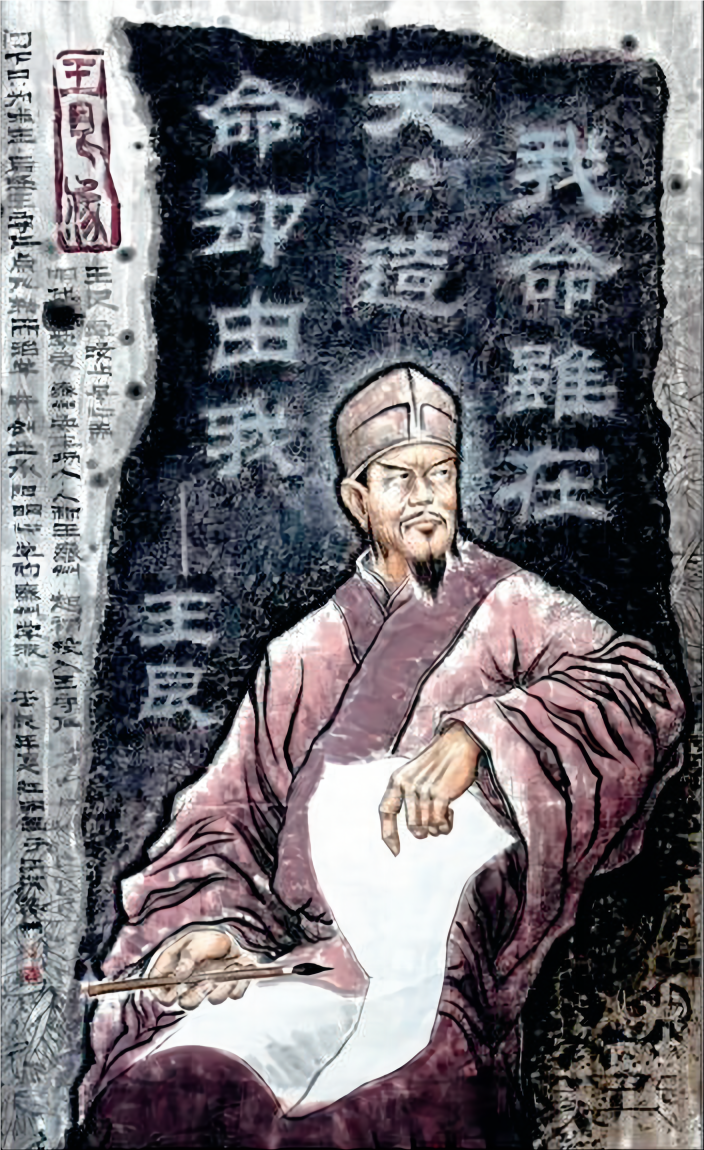
王艮名言:我命虽在天,造命却由我 如前文所述,宋儒已经为圣人和普通人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在理学家们看来,这座桥梁就是作为万物本源的“天理”,它在人内心的具体体现就是所谓“天理之性”。圣人与普通人的区别仅在于“人欲”对于内心“天理之性”的遮蔽与否。因此,普通人需要通过对万事万物的体悟来领会天理,规范人心,这就是所谓的“格物穷理”。而到了王阳明则强调:心是万物的本源,心外无理,“天理”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心”亦即“良知”,因此不必再借外物,去追求一个外在的天理来规范人心,故其理论叫做“心学”。同样是“存天理,灭人欲”,程朱理学追求外在的天理,主张心归于理,阳明心学强调内心的良知,主张理归于心。在对“天理”的体认上,阳明心学更注重内心的直觉,对“天理”和“人欲”的界定更加主观,从而将当时的人们带到了一个挣脱个性束缚的临界点,而完成这一突破的就是泰州学派。作为阳明心学传人,王艮认为“百姓日用即道”:形而上的“道”(天理)存在于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和自然欲求中,普通人与圣人的区别只是“愚夫愚妇……日用而不知”罢了。此外,他还提出“己身”为家国天下之本的思想。这样,在王艮这里,圣人与普通人之间的鸿沟被完全抹平,儒家理想也被彻底世俗化了。这种对个人主体价值的肯定,充分激发起人的主观能动性。王艮的传人很多来自社会底层,他们张扬个性,以“大我”的精神,掀起新的思想解放浪潮。泰州学派也因此被认为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先驱。 从汉唐儒家带有贵族印记,囿于经典章句的“经学”,到程朱理学强调内心体悟的“理本论”,再到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的“心本论”,直至泰州学派的“身本论”,儒家思想对个人主体性的彰显不断向前突破,却又一脉相承。开启这一世俗化思潮的是以胡瑗为代表的宋初诸儒,至晚明则达到高峰。正是由于有很多像胡瑗、王艮这样有着浓郁民间色彩,游走于正统体制内外的所谓边缘士人的存在,才使得主流儒家思想得以离开宫廷和书斋,不断地走向大众,由此激发起新的思想火花,一波又一波地汇入主流文化,推动其向前发展。 |
|